
我上世纪90年代,我住在纽约市的那个街区混乱不堪。从我的窗户,我目睹了许多毒品交易,一次刺杀,以及一次枪击的后果。7月4日,这场骚乱戏剧性地升级,当时在别的地方过夜是个好主意。但有一天,我的旅行计划泡汤了。
当我从二楼的窗户往外看的时候,楼下街上的两个年轻人开始向对面公寓敞开的窗户投掷樱桃炸弹爆竹。几分钟后,其中一人跳了起来,抓住逃生梯,爬上楼梯,穿过敞开的窗户进入公寓。他的朋友跟着他。
这比平常的不守规矩要严重得多,所以我打了911报告发生的事情和街对面大楼的地址。调度员想要我的地址,所以我也提供了。
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呼啸而来。但是警官们很困惑——他们想进入我的大楼,而不是街对面的大楼。我听到蜂鸣器的声音,大楼的外门打开了,然后两个警察冲上楼梯来到我的平台。我想告诉他们,他们走错楼了,所以我走到门口,打开了门锁。我推开门,看到两支手枪正对着我的脸,就在几英尺外,两个警察准备开枪。他们立刻放下手。
那一刻有两件事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一是他们有多害怕。我对那一刻的闪光灯记忆是两个枪口,两张惊恐的脸。
另一个是它们的反应速度。这与我怎么移动、我说了什么、手里拿着什么没有关系;这是瞬间的反应。“街对面!”我发出嘘声,他们轰隆一声下了楼梯,穿过街道。(爆竹少年早就走了。)
那些警官没把我的头爆掉也不是什么好运气。这是行动中的内隐偏见——一种闪电般快速的自动认知过程,影响了人类的决策。警察一看到我这个白人女性,就立刻认定我不构成威胁。
在这个案例中,他们是对的,但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一名警官仅仅因为他的身份,就将一名无辜的黑人男子视为危险人物,结果此人遭到枪击或杀害。如果我是一个黑人,做了同样愚蠢、无辜的事——当着一个自以为处于危险境地的警察的面打开我的门——那我可能就完蛋了。
内隐偏见是这样一个事实的产物:人们不断地对他人做出无意识的判断,这些判断依赖于刻板印象和其他一刀切的公式。这些刻板印象是一种捷径,一种快速预测别人将要做什么的方法;他们速度很快,但经常出错。在压力和时间压力下,比如当警察害怕被攻击时,它们对认知能力有特别强大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积累了大量证据,证明了这些偏见的力量和普遍性。最著名的实验室测量法,内隐联想测试(IAT),你可以自己试试.它的许多变体被设计来衡量你可能有但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联想的强度;最著名的版本揭示了对非裔美国人隐含的种族偏见。当被要求将令人愉快的词语和白人面孔配对时,白人的反应速度略快于将令人愉快的词语和黑人面孔配对时。亚裔美国人对白人的反应类似,大约一半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对白人表现出温和的偏见。该测试被认为反映了一种对白人的自动认知偏好。
这些自动的判断甚至可能与有意识的信念相矛盾。一个人可能是有意识的反种族主义,但仍然无意识地以不公平或偏见的方式回应另一个种族的人。社会心理学家说,这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的文化中的结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并内化了刻板印象。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和他的同事们说:“我们生活在渗入我们大脑的刻板印象的海洋中。创建IAT。“构成内隐偏见的关联是在一生中获得的。”
隐性偏见现在是执法和企业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流行词。美国司法部指出,执法部门将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列为嫌疑人的主要原因是隐性偏见。它甚至被认为是问题在9月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中。所以警察部门和大公司喜欢脸谱网可口可乐自豪地描述了他们为了“消除”员工的偏见而推出的举措,以及他们正在采用的研讨会和培训课程。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内隐偏见可以永久消除,也没有证据表明消除它的最佳方法。
一个有明显偏见的人有时会被说服改变观点。但是说服对无意识的刻板印象不起作用,因为人们通常不知道他们有这些刻板印象。仅仅告诉某人关于内隐偏见是不够的。仅仅指示某人抑制他们的反应是不起作用的;太根深蒂固了。格林沃尔德说:“我们已经知道,没有简单的遗忘方法。”“这并不是说不可能,但没有人展示过如何做到这一点。”
超过600项研究探索了减少内隐偏见的各种方法。这项研究表明,偏见可能是可塑的。但对于哪种技术最有效、最持久,以及它们是否适用于现实世界,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2010年,社会心理学家举办了一场竞赛,要求同事们提交消除偏见的最佳想法。22名研究人员测试了17种最好的方法,如提高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鼓励对白人的负面印象,培养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感,指导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世界,或加强平等主义的感觉。
通过门户网站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7万人。只有八个通过对IAT反应时间的适度改变,技术降低了内隐偏见。最成功的方法是将非裔美国人与积极的故事或形象联系起来,或将白人与消极的故事或形象联系起来,这些方法往往是生动的,高度个人化的。2016年的一篇后续论文发现,即使是有效的技术,也没有任何效果持续几天。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后、社会心理学家卡尔文·赖(Calvin Lai)说:“这两项发现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惊讶和沮丧。”“它们都没有持久性,这让我非常震惊。”
鉴于这样的结果,学术研究人员表示,对偏见的了解还不足以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利哈伊大学研究无意识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家戈登·莫斯科维茨(Gordon Moskowitz)说:“如果有一个清晰、容易实施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没有。”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意图良好但设计糟糕的创造意识的努力可以会适得其反,培养的不满。
尽管如此,多元化顾问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展反偏见培训警察部门在大公司里。美国司法部6月宣布,它有超过23000名执法人员和5800名律师会训练识别和处理内隐偏见。课程通常提供一到六个小时的教育,通常包括教育和技能培训。
“我们并不是在帮助他们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忘记他们的偏见,”南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副教授、美国犯罪学院的首席执行官洛里·弗里德尔说公平公正的警务工作这家咨询公司主动与美国司法部合作。“没有什么能消除他们一生形成的偏见。我们教授的策略和工具从长远来看可以减少偏见。”弗里德尔说,公司每周都有几次培训,生意很好
Fridell说,FAIP计划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她举了接触假说的例子,该假说预测,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在积极的环境中互动,偏见就会减少。一些研究表明,即使是想象这种群体间的接触也能减少焦虑并改善态度,尽管在Lai的实验中,试图触发这一效应的干预并未导致参与者的IAT结果发生任何变化。
Fridell说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你不会期望在实验室里几个小时内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反,她说,他们为新兵和巡警开设的课程包括6个小时的培训,引入内隐偏见的概念,增加警官减少偏见的动机,并阻止它被激活,弗里德尔说。FAIP没有正式评估其培训的影响;弗里德尔说,她正在为这样一个项目寻求拨款支持。
咨询公司教授的课程库克罗斯略有不同,针对的是公司、大型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创始合伙人霍华德•罗斯(Howard Ross)表示,该项目的目标是提供有关大脑如何工作和决策如何发生的教育,并教授干预措施,帮助人们减缓或减轻自己的反应。“我们努力做的不是消除人们的偏见或消除偏见,”罗斯说。“根据研究,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能做的是让人们明白,他们可以学会观察自己的偏见,并不时地摆脱它们。”
技巧包括有意识的呼吸练习,鼓励人们使用审慎的思考过程,而不是自动或情绪反应,以及启动工具,鼓励人们练习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到的技能。该项目为人们提供两分钟的视频,可以在手机上播放,并建议客户定期回顾关于偏见的经验教训,或者在重要会议或人事决定之前。
“我认为这有百分之百的影响吗?当然不是,”他说。“但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罗斯说,这家咨询公司不收集数据来评估其项目,但它的一些客户会。据他说,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客户成功地增加了女性被聘用或晋升的比例。
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反弹,社会心理学家普遍对营利性培训持怀疑态度。格林沃尔德说:“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但不能通过naïve那些从心理上不了解情况的人所尝试的方法来解决。”
在莫斯科维茨看来,消除偏见的项目应该只由心理学专家创建;一些学者已经创建了这样的项目,包括隐式计划的研究人员,但这些学术项目无法开始满足需求。此外,莫斯科维茨说,任何教授无偏倚技术的项目都应该收集数据。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只是挥杆而已,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否有效。”“我们所处的阶段是将细致入微的实验室工作转化为现场环境,这需要一些专业知识。但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捞钱行为。”
至于警官培训,赖说,“我担心这可能不会有效。但缺乏证据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效的,只是还没有被研究过。”
赖、格林沃尔德、莫斯科维茨和其他人并不认为偏见是棘手的,他们正在继续测试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的方法。更密集或更持久的项目可能更成功;以儿童为目标可能更有效。莫斯科维茨认为,挖掘动机和目标是关键。“隐式计划”的研究总监赖表示,他的团队“重新开始”,正在研究儿童教育等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莫斯科维茨和他的研究伙伴、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杰夫·斯通(Jeff Stone)正在该大学医学院测试一种干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数据,看看对一年级学生的培训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似乎确实有效的是黑客和变通方法,从一开始就防止了偏见的触发。最著名的例子是盲试,交响乐团从屏幕后面评估申请者,这样性别就不会影响决策。这种方法增加了女性从第一轮进入第二轮的机会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采取了盲目审查的做法,从求职者的简历中去掉名字。另一些公司则采用有一系列问题的结构化面试,使招聘过程更受数据驱动,不太容易产生主观印象。库克•罗斯为这些结构性调整提出了建议,以帮助企业更公平地进行绩效评估和面试。警察部门可以引入基于规则的标准来指导交通拦截或逮捕,这可能会减少偏见的影响。
这些变通方案是为受控环境设计的,比如办公室,或者甚至是一个常规的交通站点。很难想象他们会在黑暗的走廊里帮忙,当一个压力重重的警察听到开门的声音并拔出了枪。事实上,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能克服那一刻的恐惧和肾上腺素。但研究偏见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他们了解得更多,这是可能的。“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格林沃尔德说。“我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Kat麦高文是他是驻在加州伯克利和纽约市的独立记者。在推特上找到她@mcgowankat.
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文章投递到您的收件箱!
看: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说,对警察暴力的愤怒,部分是由于反思的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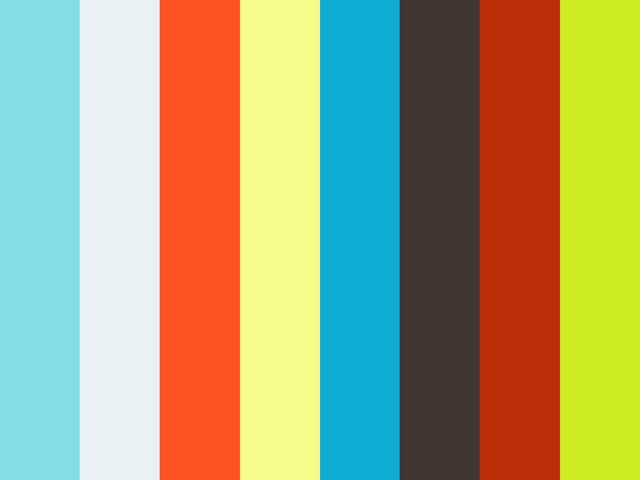
封面照片是由来自Flickr的Thomas Haw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