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科学史上我最喜欢的时刻之一来自一个名字很难再提的人:罗伯特·拉斯本·威尔逊。1967年,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他成为当时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后来为了纪念恩里科·费米而改名为费米实验室)的首任主任。两年后,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邀请他为其大约2.5亿美元的成本辩护。参议员约翰·帕斯托雷,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问威尔逊,“在这个加速器的希望中是否有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东西?”
威尔逊回答说:“不,先生,我不这么认为。”
也许给了他另一次机会,帕斯托雷换了一句话:“在这场比赛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处于与俄罗斯人竞争的地位?”
威尔逊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正在发展的技术。”。“否则,它与:我们是好画家、好雕塑家、伟大诗人吗?它与保卫国家没有直接关系除了让它值得捍卫我。”(斜体)。
威尔逊似乎认为,这个加速器的工程师,以及用它研究自然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重要。这会使工程学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吗?顺便说一下,奥林学院总统的理查德·k·米勒(Richard K. Miller)描述了一位工程师,你可能会这么想。他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鹦鹉螺最近,在他的《Ingenious》杂志的采访中,“它始于视觉。除非你对新事物有远见,对从未有过的事物有激情去完成它,否则我们不相信你是一个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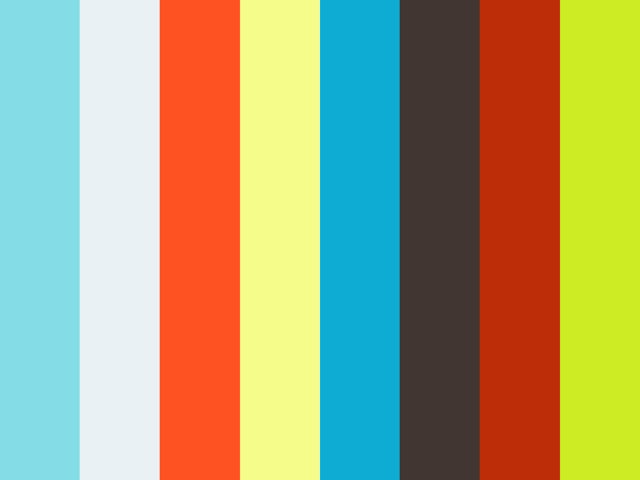
你可以听清楚我们和米勒的谈话在这里.
Brian Gallagher是Nautilus博客Facts So Romantic的编辑。在Twitter上关注他@布里昂加11gher.
主要形象由克里斯·史密斯通过Flickr.
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文章投递到您的收件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