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y wife Ingrid and I had been in Aburi, Ghana for just over a week when our host, Kwame Obeng, informed me that I’d be joining the royal drummers for a performance at the chief’s palace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in celebration of an important holy day.
这并不是因为如果我是措手不及。我第一次见到OBENG三年前,当他来到多伦多执教加纳移民和一个孤独的西方人(我)作出了一个鼓乐艺术团。我们成了亲密:OBENG叫我mi nua,或“我的兄弟”在TWI,他族群的语言,阿肯。当他的签证过期到期时,他邀请我继续与他一起在阿布里回家,一个小镇坐落在临时Akuapem山丘上。两年后,我把他带到了他的邀请。现在是时候向他展示我能做的事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惊喜。我永远不会发现它是一个惊喜对欧能感到惊讶。
演出那天,奥本让我和他的侄子站在一对巨大的桶形雕塑前,他的侄子名叫夸梅·安特维(Kwame Antwi)兄弟鼓肩的鼓。每个兄弟从一个5英尺长的镂空树干雕刻,两者都涂上了一股光泽的黑色,并用黄铜铆钉固定在红色天鹅绒上。就在我们面前和我们的左边,欧伦本人站在一双大规模的,脚轮形状之前阿图潘与羚羊皮头鼓。直接在我们身后,年轻的男孩和中年男子的四重奏演奏三个小鼓和铁钟。他们的节奏部分,而两个Kwames和我形成了前线。
我别无选择,只能在鼓上士兵。当我这样做时,我也努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演出开始时,夸梅·安特维和我开始用树枝做成的L形长棍猛击厚厚的牛皮头。我们真是天生一对:他又长又瘦又黑,我又矮又软又白。庭院另一端的高台上,逐渐挤满了身穿长袍和礼服的酋长和宫廷官员,这些衣服都有不同的颜色:绿松石、猩红、钴、栗色。几乎没有闲聊。相反,我们打鼓的时候,我们的观众静静地听着,各种名人站起来发表演讲,向他们的祖先祈祷。
为什么每个人今天都没有黑皮肤?
皮肤似乎是人类的一种表面特征,但它是我们遇到任何人时首先注意到的东西。尼娜·雅布隆斯基(Nina Jablonski)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她正在给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上人体解剖学课……阅读更多
节奏在大上演奏兄弟鼓由几组模式组成,由两个鼓手一起执行,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长更复杂。起初,我的中风和安特维的不相上下。但当我们进入更长的和更复杂的材料时,事情完全偏离了轨道。突然间,安特维似乎加入了我从未听过的节奏。我试着跟上他,模仿他的手的动作,尽管我不太清楚他在弹什么。
但我做不到。站在聚集在一起的皇室成员面前,我慢慢明白了真相:我本应该在阿布里公开演奏的节奏与奥本在多伦多教给我的不一样,而奥本在前一天的一次简短的私人课上为英格丽德和我重复了这些节奏。相反,这些节奏包括了大量的节奏这些材料与迄今为止他向我们展示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如此不同,以至于我无法在最激烈的时刻理解它们,更不用说执行它们了。但似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
“亚历克斯,有什么问题?”安特尤在休息期间,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坐下来。“你昨天玩了这些,没问题。”
“节奏是不同的,”我说,仍然为自己的首次公开亮相完全失败而震惊。
“什么?”
“这些节奏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我在多伦多打的人。他们不是我们在昨天我们的教训与OBENG玩过的人“。
“当然他们是一样的,”安特尤说。“只有更快!”
这将是我们加纳朋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的标准线:节奏是一样的,只有更快!但他们不是。由于我们的主人继续坚持认为,他们教导了我正确的节奏,我在绩效之后的表现:仪式,在葬礼上,有时是巨大的人群。我无法停止表演 - 我们将在千里学习这场音乐,我们在集团中的存在是对鄂议的尊敬的声望来源,但酋长和宫殿官员知道Fontomfrom肯定必须意识到我永远僵住了,即使他们不容透明,只是“woaye正面!(“干得好!”)。
我别无选择,只能在鼓上士兵。当我这样做时,我也努力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最终,我将其煮到两种选择:要么我们对构成音乐繁体和差异的思考,我们都有彻底发散的想法,关于给出了一个音乐它的独特身份和听觉签名;或者由于未知的原因,obeng是故意从Ingrid和我隐瞒完整节奏。它是欺骗还是精神上的断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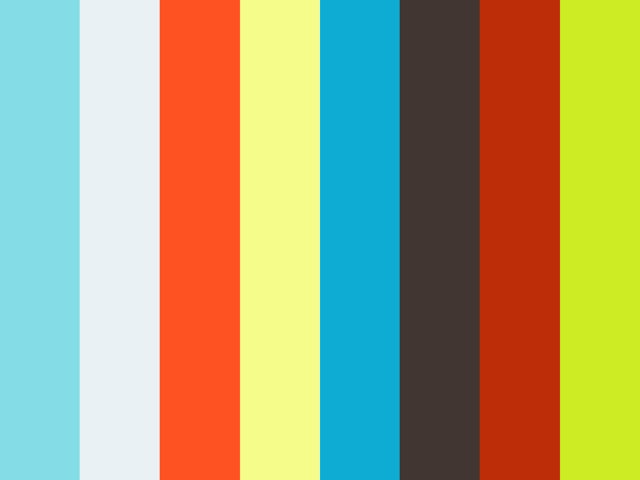
米Ÿ混乱和我突然无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玩音乐的风格,被称为Fontomfrom这是阿肯人的鸡尾酒钢琴。但它不是。每当首领们因公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皇家鼓就会响起。它们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官职的主要装备。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兄弟和阿图潘鼓不只是让音乐跳舞。他们说话了。字面上地。
TWI是一种语气语言,如普通话:每个音节都有自己的音高,每个单词或短语它自己独特的旋律。改变这些音调,改变那些旋律,也改变了这些词的含义。像问一个人的名字一样简单的东西成为鸟类的运动。

通过模仿特维人的音调和节奏,阿肯人可以用他们的乐器“说话”——他们的喇叭和小号,他们的鼓和铃铛——几乎和他们用嘴说话一样清晰。的阿图潘产生两个不同的音高,特别适合这项任务;但是兄弟也可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宫殿的人群已经如此安静:他们正在听老鼓的话。西非和中非的现象,普遍存在,被称为替代言论。它可以为即使是最简单的音乐也可以添加一层语义深度。
每次,行政,娜娜夸西Djan,起身走了一圈庭院,例如,两个Kwames和我搞一个小的呼叫和应答。
kwame obeng:物料清单bom
夸梅·安特维和我:BRRM BRRM!
节奏短语bom bom BRRM BRRM,bom bom BRRM BRRM它有一个很好的节奏,可以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填充,当首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是乐队主要的会说话的鼓手诚恳地恳求道:娜娜,bre正好!娜娜,bre正好!“酋长,慢点!酋长,小心点!”如果酋长在公共场合绊倒,那就是运气不好的迹象。所以我们要求他小心脚下。
鼓不只是与生活说话,而且还对死者:离开这个尘世的崇敬的祖先,但继续影响他们的亲属的事务。阿肯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永远观看他们的,必须永远与祈祷,产品和其他记忆一起安置。他们还认为他们的祖先对鼓的声音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澳门人鼓手通常非常注意避免错误的原因之一。通过说错话,你不会想愤怒你的祖先。在过去,雄鹿皇家鼓手很可能会被切断。所以当我在宫殿那天撒上安特利的人屠宰时,我不仅仅是让小组声音不好 - 我在讲话,艺术和宗教都交织在那里粘在丰富的文化系统的齿轮中。我的心在我的耳朵里走开了鼓时,我的心在我的耳朵里砰砰直跳,我的错误仍然响了庭院。
这个音乐很重要。那么,为什么鄂··鄂省坚持扣留信息,这些信息将阻止我们吹嘘我们在加纳我们在加纳的每一个表现?他有一些难题吗?或者是Akan音乐的一些基本方面,使其在基本水平,心理上,甚至神经看起来对我们不透明,这是不透明的?

我ngrid和我都毕业的学生在伊利诺伊大学,我们在1997年夏天离开之前,加纳我是博士候选人在民族音乐学,是一种音乐人类学,和英格丽正在完成一项打击乐博士学位。换句话说,我们不完全的音乐黑客。但难度Fontomfrom是意外,和出色的。
与西方非洲舞蹈课上经常伴随的鼓声不同,Fontomfrom没有特别强的凹槽。但像大多数西非鼓一样,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运动部分,从长而复杂的模式兄弟和阿图潘到短的,高度重复的模式起到对较小的鼓和铁钟。所有这些节奏联锁;通常情况下,他们完成彼此,一个桶灌装的声音在别人的沉默,产生意想不到的图案,像织锦个人股。
Fontomfrom节奏也可以奇怪含糊不清。例如,你可能会认为你正在玩一个华尔兹(一两个三,一两三个),而你旁边的家伙听起来好像他正在演奏三月(一两个,一二)。事实上,如果你足够长时间听他,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并决定你,也真的在玩游戏。从那意义上,玩耍FontomfromEnsemble就像是在eScher石英仪的声音版本内:当你将注意力从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时,整个图片似乎改变了。
试图破译那些简短的令人费解的细分,就像试图抓住刀刀一样。
的兄弟然而,我突然预计在加纳举行的模式是在他们自己的联盟中。他们的比特不仅仅是有节奏地含糊的;它们是有节奏的功能失调。音乐学家会说他们是Ametric的,或者缺乏与任何类型的稳定脉冲有明显的关系。但对他们来说绝对有某种逻辑,因为每当两个人真正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接管了兄弟,他们不仅做到了完美的一致性;他们还以完美的一致性与其他鼓手的角色矩阵协调出入。显然,他们知道并听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它并没有帮助,英格里德和我几乎无法听到bommaa r一点也不奇怪。虽然我们通常与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庭鼓手搭档表演,但我们也经常被告知“更大声”、“更快”和“更有力”,这只会让我们更难理解搭档演奏的节奏(其他人也更容易听到我们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在其他情况下很容易做到:很难描述一个声音有多大Fontomfrom合奏是,它的羊毛铃铛,它的刺穿小鼓,它的蓬勃发展阿图潘和它的雷鸣兄弟.更糟糕的是,Nana Djan Kwasi的宫殿庭院是一个巨大的回声室。我们录制了我们在法庭上给出的每种表现,但大鼓的声音在混凝土墙壁和波纹金属屋顶周围完全超载了我们的麦克风,让我们的所有录音都变成了嚎叫的混乱。
在我们的停留快结束时,Nana Djan Kwasi法庭的一位友好的副长官允许我们在附近一个村庄的更可控的条件下录制Obeng和其他皇家鼓手。在这些磁带的帮助下,英格丽德几乎把节奏降下来了。她一边听着,一边低声唱着:“哒、哒、哒、哒、哒、哒……”
“嘿,艾尔,这真的开始有意义了!”我现在可以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了
“我也是,”我说。“但有几个地方他们仍然失去了我。”
“你的意思是这样?”Ingrid说,为我提出了一段录像带。
“是的,”我微微眯起眼睛说。“那是什么鬼东西?”
西方音乐与自己的符号系统一起演变,使西方音乐家倾向于听到他们可以阅读的内容,并阅读他们可以听到的内容。它没有发展以反映有节奏的微妙之处Fontomfrom. 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很短的片段兄弟我们无法准确记录的节奏;就我们的音乐系统而言,它们并不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听不清他们的声音:他们听起来很模糊,就像印象派风景画中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问题不在我们的耳朵,而在我们的大脑。
麦考之大学的心理学家比尔汤普森专门从事音乐感知和认知(以及在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毕业生助理),建议我们可能缺乏精神模板或架构,用于分类这些节奏,因此无法清楚地察觉。“节奏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比尔告诉我,“因为我的感觉是”听到“特定节奏模式的能力是首先,最重要的是”预测“在不同时间跨越的能力。”我n the absence of such a schema, Bill adds, “we cannot predict what will come next, and have the experience of ‘not being able to hear the rhythm.’ Of course we ‘hear’ the rhythm in a literal sense, but we just can’t predict the unfolding pattern.” The ethnomusicologist David Locke, a specialist in West African drumming at Tufts University, experienced something similar when studying a form ofFontomfrom被称为GA的族裔群体。呼应汤普森,他认为“缺乏组织的心态”可以使其“难以察觉耳朵接受的东西”。
无论是什么原因,试图破译那些简短,令人费解的细分市场就像试图抓住一个坠落的刀。当我意识到我遇到盲点的观察时,我仍然记得震惊的感觉。好像一个高度选择性的中风都抢劫了我的能力阅读字母Z或看到颜色紫色。那些节奏,其中一些人在眨眼之间传递,就在我的肯之外。
所以,奥本是否教会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可能并不重要;就算他打了,我也怀疑我们能不能打。但问题是:为什么奥本没有承认他私下教给我们的模式不是我们期望在公共场合演奏的节奏?

一个经过一番努力,英格丽德和我设法说服了夸梅·安特维,我在大兄弟教我们在公开表演中应该演奏的延伸模式——那些Kwame Obeng甚至拒绝承认存在的模式,而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模仿不出来的模式。但这种经历只会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而不是播放我们非常想听的音乐,甚至是播放英格丽德所说的“可笑的婴儿版”兄弟欧登坚持向我们展示我们的课程,Antwi扮演了另一种简化的变化。Antwi的课程版本比欧能更复杂,但仍然没有真正的交易。然而,当我尽可能多地说,安特里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他的纯真。
“是的,它是一样的,”他说。
“它听起来不一样。这不是kwame obeng在我们的课程中向我们展示他,也,“我说。
“是的,他们是一样的!”他坚持。
“和什么一样?”我想尖叫。
也许问题在于大脑的代词功能Fontomfrom.如果这些难以捉摸的节奏没有语义内容,那么Obeng和Antwi并不认为它们的缺失(或存在)构成了有意义的差异,那会怎么样呢?这可能会使“课程模式”和“表现模式”等同于我们的老师,即使他们在我们看来是明显不同的实体。或者,也许两个夸梅斯是根据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标准来评估音乐身份的——这些标准对我们来说就像神秘的节奏本身一样陌生。
我以为我一直在窃听一些无害的舞蹈节奏,当时我一直在参加关于仪式屠杀儿童的简短音频。
绝望的洞察力,Ingrid和我转向J.H.K.NKEIA是一位着名的民族武士学家,当时是国际非洲音乐中心董事,加纳大学的国际音乐中心。内洁是我的英雄:来自Ashanti地区的阿罐,他在20世纪50年代在Akuapem进行了实地,并在Akan Drumming上写了Ominomin工作。当我们告诉他关于简化的时候,他并没有眨眼睛兄弟鄂永和安特尤试图在我们的课程中试图将其作为真实的东西传递。但他确实笑了笑。
“它们可能被简化了,但它们仍然是一样的,”他说。
“因为他们分享了某些节奏的主题?”英格丽德问。
“是的,有这一点。但不仅如此,”他说。“A片由许多借给它身份不同元件组成。如果这些元素存在,它是相同的。如果不是,它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概念,你将有挣扎“。
但是哪些元素构成了节奏的特性呢?当Obeng来到多伦多时,他教我和我的鼓手同伴们在小乐器上演奏的伴奏模式的基本版本和交替版本,把区别清楚地表达出来。然而,在阿布里,奥本甚至不承认基本的区别兄弟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节奏——他以前在多伦多教过我的节奏,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中表演过的节奏——以及我们应该在公共场合演奏的更长、更复杂的节奏。如果我知道Obeng在每个例子中所关注的是什么,也许我就能理解它们之间的明显区别。但我不知道,也许,考虑到很难识别Fontomfrom节奏开始,我不能。
或者,也许我们的老师只是搞砸了我们。

米任何一个非洲社会都将他们的传统知识隐藏在秘密之中,而这些秘密的守护者——长老、牧师、首领——往往会逐渐地揭露它们,随着一个人在更高层次的信任中不断提升,一点点地泄露它们。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本身固有的敏感性,也因为它的深奥本质给拥有它的人带来了权力和威望。艺术历史学家玛丽·h·努特(Mary H. noter,现为玛丽·努特·罗伯茨(Mary noter Roberts))在她的书中写道:“对非洲秘密的研究表明,秘密的内容不如秘密作为一种策略重要。秘密:隐藏和揭示的非洲艺术.“尽管秘密的内容可能被保守和隐藏,但秘密的存在往往被大肆宣扬。拥有秘密知识,并表明自己拥有秘密知识,是一种力量。”
这可以描述音乐知识如何在AKUAPEM治疗?也许奥格不愿意教导我们缺少的节奏,因为他们构成了某种特权信息。也许他们作为一个公开秘密的地位 - 他和另一个法院鼓手将在公开场合发挥作用,但我们不允许在私人服务中学于努力突出自己的权威,以及我们自己的地位为Neophytes。
我们已经经历了这种隐藏和启示录的动态。在我们在多伦多的时间在一起,鄂省从未如此介绍过那个较小的乐器Fontomfrom“谈到”就像他们的大表兄弟。然后,有一天在阿布里,当英格丽和我在宫中帮助OBENG移动Fontomfrom鼓声响起,他不经意间透露了铁钟和三个小鼓在说什么。这是一场全面展开的对话:
wanko一个wobeko。
WOTO,WOBETO。
莫夫拉马·库姆是谁?
Pren Pren,Pren Pren。
“你会去,即使你不想去。”
“你会掉下去,你会掉下去的。”
“你杀了小孩吗?”
“刚才,刚才。”
“这是什么意思?”英格丽德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孩子?”
奥本说:“这是关于远古时代,祖先制造‘药’。”。他接着描述了人类曾经是如何在宫殿里献祭的,这是我以前只在人类学研究和历史文献中读到的。不用说,我们都大吃一惊,尤其是我。几年来,我以为自己一直在敲打一些无害的舞蹈节奏,而事实上,我一直在参与一个简短的关于屠杀儿童仪式的音乐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kwame obeng选择特定的时刻来启发我们,但我怀疑它是偶然的。也许,对我们来说,Ingrid和我以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我们的价值。
还有一次,在一个葬礼上,我问夸梅·安特维(Kwame Antwi),他和其他许多人在凉鞋的背带上戴的那个小装饰品是否有什么意义。
“是的,”他说。
“什么?”我问。
”Aburuburuw Nkosua.,“ 他说。“这是鸟鸡蛋的名字。”
“这是谚语吗?”
“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们将不得不问夸OBENG。”
所以我们所做的。
OBENG回应在特维语:“如果是写,写;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又转向安特维。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装饰品被称为什么?”我问。
“是的,”他说。
“但是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只有那些谁与王室移动“。
安特维是奥本的侄子,也是他在宫廷里的副手。以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他都花了大量时间与王室成员来往。但即使是他也不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一句谚语的意思,而这句谚语大部分时间都粘在他的脚上。
音乐中缺失的复杂性代表了我自己的神秘谚语,我还没有获得学习权的东西?这是这个过程的所有部分,我只能通过自己弄清楚音乐来展示我的价值吗?或者是obeng不愿意为其他原因教我缺少的节奏,但同样不愿意明确转动我?
T这是我目前所能找到的。18年后的今天,事后看来,奥本行为的原因和那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一样让我难以理解兄弟节奏被证明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训。
作为一名音乐家和民族音乐学家,我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努力,我最终会了解我们主持人的音乐和音乐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相信这一点;这样做是我自己身份认同感的核心,就像任何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做实地调查的人一样。当然,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中没有一位提出我(或其他任何人)可能会遇到一群人,他们的音乐和动机会顽固地抵制分析和解释。在这个极度互联的时代,当曾经遥远的土地离我们只有一次廉价的飞行或一个网页之遥时,人们很容易认为,跨文化理解的所有障碍正在逐渐消失;不再有陌生人这样的东西,只有我们还没有在谷歌搜索过或在探索频道上见过的人。
这是一种幻觉。毫无疑问:有很多人,生活在很多地方,仍然巨大的谜题给我们,廉价的机票或者没有。这绝不是一件坏事。相反 - 它是人类多样性范围和人类理解的估算规则。我在阿布里的经历可能一直令人沮丧,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不再假设可以克服所有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我也不能认为我真的,真的,真正进入别人的头脑,看看(或听到)他们所做的纯粹理性和遗嘱,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由于这些原因,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对强度有,我们目睹了动物的牺牲和降神附体,遇到的文化财富和物质贫困在西方很少见,并且遭受的那种既不是我们的激进文化冲击之前曾经历过,和haven’t again since—Aburi still fills me with a sense of awe. And I know that Ingrid feels the same way.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hings that shaped us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couple, we always return to Ghana, and the mystery of those兄弟节奏。
Alexander Gelfand是一位自由作家,恢复在纽约市的畜禽学家。他正在加纳他的时间备忘录。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15年11月的《身份》杂志上。














































































































